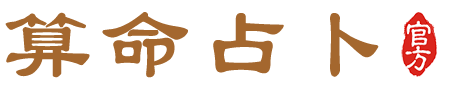說名道姓:十八、姓名貴賤論
十八 《百家姓》是按貴賤排列的嗎——姓名貴賤論
若說姓名也有貴賤之分,恐怕不少人要嗤之以鼻,但事實畢竟不會屈於偏見。姓氏與人名的貴賤之分不僅確實存在,而且源源流長。畸形的封建社會定然有其畸形的產兒,以貴賤論姓名只不過是封建宗法門閥制度的雕蟲小技。
姓名貴賤論分名和姓兩條來敘述,這裡先講講姓氏的貴賤淵源。
南宋史學家鄭樵有《通志·氏族略》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之氏。陪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賤也。”
這段話明白地告訴後人姓氏形成之初,其主要目的就是“明貴賤”和“別婚姻”,上古三代“貴者有氏”,只有貴族才有姓氏,一般平民百姓不得擁有,奴隸就更不用說了。有姓氏的貴族,掌有朝政大權,當時被稱為“百姓”,所以那時“百姓”一詞,是對有爵祿官職的人的泛稱,指百官,與現在的意義恰好相反。即使“百姓”之族,到了周朝也開始有貴賤之分。百姓中最尊貴的一姓為王族姬姓。姬姓占有的封地最多,政治權力最大,姜、姒、子等姓次之,以後便是掌管手工業技術、管理工程的低級“百姓”。
周朝後期,經濟基礎的變化引起上層建築的波動,姓氏得以從少數人手上分離出來,成為全民共享的公共財物。許多人漸漸認識到,姓氏只是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代表自身與家族的符號,組成姓氏的字不過是單字詞,根本不與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和含義發生任何聯繫。
但是,正如俗話所示:百足之蟲,僵而不死。以“明貴賤”為由產生的姓氏,在封建社會這個“等級制度”的溫床里不可能睡個安穩覺,就在它剛剛合眼不足百年時,兩漢的劉姓皇族就把它從熱被窩裡攪醒,堂而皇之地把它扶上史輦加以開發利用。他們依“因生以賜姓”舊律,引經據典來論證劉氏的高貴血統和非凡出生,其根據是:《左傳》載帝堯唐陶氏之後、晉國大夫士會曾一度出奔秦國,其家族亦居於秦,後士會歸晉,留在秦國的家族就改稱為“劉氏”,因而劉氏乃帝堯後裔,其血統決定他是要稱王稱帝的。為了推廣他們的“姓氏貴賤說”,劉漢王朝開始將自己的劉姓賜給有功於朝的文臣武衛,讓他們與自己一同享受“國姓爺”的伏特;凡劉姓全家皆免其徭役。
劉氏開風氣之先,後來者蜂湧而至。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後,派人到處放風說:“王氏”也出於帝堯,坐龍庭非他莫屬,如此一打一鬧,姓氏的門第貴賤觀念深入人心,某人一有名氣,人們便自發地為其“尋根問祖”,考察其為某某名門貴族後代。東漢末年,“亂世英雄起四方”,“織席販履小兒”劉備在政治角逐中成為三鼎之一,於是王朝史官遍查百史,推算出劉玄德乃當今皇帝的長輩,尊為皇叔。後來又嫌“皇叔”之名太虛,乾脆做了個實實在在的皇帝。
姓氏高低貴賤之別,經兩漢的“沉渣浮起”到魏晉南北朝經長足發展,臻於登峰造極地步。有唐劉禹錫懷古詩《鳥衣夢》為證: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西晉末年,司馬睿帝帶著大批豪門貴族逃到江南建立了東晉政權,這些有功之臣多是王、謝、袁、蕭四大姓,他們依仗開國之功,掠奪權位,為後代開闢了高貴的門第。此後,四大姓執掌南京政權達兩百年,《烏衣巷》中的王謝指的是開國之勛王尋與謝安兩大家族,他們世居南京鳥衣巷,常手執塵尾,高談闊論儒佛之學,吟詩賦詞,附庸風雅,享盡榮華富貴。魏晉南北朝時期,“王謝”二姓就成瞭望族大姓、高門顯貴的代稱。
兩晉以往,北魏時期,定高貴大姓已形成定製。公元495年,孝文帝詳定族姓,確立了門閥系列。列鮮卑族穆、陸、賀、劉、樓、於、嵇、尉為一等士族,“勛著當世,位盡王公”;對漢族則規定:“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雲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這四姓。”具體說來,茫陽蘆氏,清河翟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四姓為最高門。據說隴西李氏聽說魏孝文帝於漢姓中“定四姓為最尊”時,急如星火,策馬晝夜兼程趕至洛陽討封,無奈盧、崔、鄭、王四姓已定矣,李氏“姓”落孫山。為撫真心,孝文帝又頒令言趙郡李氏、隴西李氏、博陵崔氏之門第也很高,隴西李氏才悻悻而去,時人因而諷刺隴西李氏為“馳李”。
隴西李氏緣何要飛奔上京討封呢?因為那時姓氏的高低直接關係到他們的社會地位、仕宦升遷、婚姻關係等。許多士族大姓憑其家庭出身,可以“平流進取,坐致公限。”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如琅琊臨沂王氏,從漢代到南朝陳代,17世數百人為高官,許多人做到丞相、吏部尚書等職,而出身寒門者哪怕你有驚人之才,也只能屈居下位,永世得不了翻身。為此西晉文人左思在《詠史》中憤筆寫道:
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西漢權貴金日磾和張安世之後代,憑籍祖上蔭功竟七世為官,而才翹當代的馮唐由於出身寒門,直至皓髮蒼顏仍屈居下位,可見姓氏貴賤惡習害人非淺。
對姓氏高低貴賤之分豈止是左思一個不滿,同朝大臣諸葛恢也是滿肚子火。一次他與丞相王導爭論姓氏先後,王導問:“為什麼世人不說葛王而說王葛呢?”諸葛恢說:“這好比說驢馬,驢在前,但驢能勝過馬嗎?”
到了唐朝李世民時,姓氏的等級觀念仍未松馳。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奉命撰寫《氏族志》,分上上至下下九等,定姓氏之高下尊卑,高氏以為李世民開明,竟斗膽定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居次。唐太宗知道後怒髮衝冠,大加斥責,欽定皇族之姓為上之上,第一等;外戚之姓為上之中,第二等;崖、鄭等大姓為上之下,為第三等。於是形成唐代李、崔、盧、鄭、王五大姓,五姓七家,自持族望,恥與他人為婚。這種情況在《西廂記》就有反映。張生一上台就自報家門:“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先人曾拜禮郭尚書;”崔鶯鶯出台便聲明自己是博陵崔相國之女,老夫人許婚外家侄子鄭恆,鄭配崔,自然是門當戶對,而張君瑞儘管是相當於外交部長高官之後,無奈姓張,並非頭等望族,所以戀愛路上困難重重,作者在戲中讓“有情人終成眷屬,”無疑是對姓氏貴賤與門第高低的一次重型炮擊。
姓氏高低之分,最有說服力的莫過於啟蒙讀物《百家姓》了。此書出自北宋初年一位不為人知的老儒之手。趙乃當朝國姓,理所當然地坐了首位;第二位是強弩射潮的吳越王錢繆之尊姓,錢乃吳越國建立者,盡有兩浙十三州之地,於是當了亞軍;第三至第八名的,孫李周吳鄭王六姓,俱是歷妃之姓,帝妃一家,同為皇室,最高貴的前八名,不許他人染指,此書即是按當時政治地位高低排列的。
姓氏貴賤在封建社會還有一種最為明顯的表現方式,那就是避諱。前文已述,李唐王朝禁止食鯉,朱明王朝禁止食豬,別的姓哪有如此威風?高貴的姓如此顯赫,低賤之於皇上賜給惡人,政敵的虺、蛸、蝮等姓,如同臉上刺了金印一樣,其命運之慘則自不待言了。姓氏的貴賤區分並非國粹,象印度的“種姓”制度與羅馬的貴族專姓制,朝鮮的“制姓氏”只讓史仕宦士族略有之”到頒姓於“八路”,無不是明證。其詳情與我國大同小異,在此不一一細言。
人名之貴賤意識遠不如姓氏流行廣泛,只在一些特權階層或特殊時期斑見於人。當然,從廣義上來講,在中國幾千年專制的歷史中,每個人分生於貴賤不同的階層,教養不同,身份有異,文野程度不同,所命的名常常從其本身即能顯其貴賤。如窮苦人家,文化程度有限,替子女命名,只好“豬兒、狗兒”地排下去;念書人腸中灌過墨水,多帶希賢、居正、子房、曲徑的一套;至於奴婢們的名字則多是“來福、來喜、萬兒、秋香”之類;王侯將相的命名當然更有講究,因為名字一旦定下來,天下人都要尊而避諱的。正因為名字本身是貴賤雅俗的標誌,所以常有些家業中興者改名以適應新的身份,如販私鹽出身的張九四、九五、九六,一旦造反稱王,也改名為張士誠、士德、士信了。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生話在哪一階層,大體都有與之相配的名字。因此廣義之姓名貴賤,可以說是非常普通的。
避諱是姓名貴賤的強證。在舊社會,命名頗多限制,魯大夫 講過五法六避,國君、聖賢、外戚和勛臣的名字明顯高人一等,神聖不可侵犯,一旦某字詞被他們取以為名,便成了他們的專利,你低他一等,為尊者諱的壓力按住你的腦門,與他同名就得改,倘有牴觸,必遭罪責。封建官僚名字如何作威作福,可想而知。在封建社會,最尊貴的名字當然是國君、聖賢、外戚和勛臣了。他們的名字往往經過史官絞盡腦汁反覆考究而來,用盡人間最貴、最美的字詞。如清皇室按精心排的字輩起名從雍正皇帝胤禛開始,分別為胤、弘、永、綿、奕、載溥、毓、恆、啟、燾、閱、增、祺。這種字輩名,“只有近支宗族,才能依此命名,其支派稍遠者,命名便不得依此行輩。”又如受漢族人名影響極大的越南,陳朝(1225—1400)帝王世系多以“日”字偏旁或火字偏旁之字為名,即“在天為日,在地為火”,象陳晃、陳
,陳暄,陳旺、陳昊等均是日為偏旁,這些美辭美名一旦被他們選用,別人不僅不能取以為名,而且還要在一切書錄口語中加以迴避,否則,罪不可恕。筆者在姓名與避諱一章中將有詳述。皇族命名不僅選盡之下好辭,而且對一些取以為名後剩下的帶有王、霸含義的詞也禁止平民使用。《容齋隨筆》云:“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老、天、君、王、帝、 聖、皇等為名字。”許多名中含有這些字的都強行改名。所謂“啟疆辟疆,王子之名”也,他們吃剩下的,你也不得覬覦。
如果僅禁幾個字倒也罷了,偏偏有些國君有了不正常的業餘愛好,象漢王莽就禁止所有的兩個字的名字,對於低賤無能、判亂投敵者賞賜二字名以示其罰。王的飛橫跋扈也太讓人忍受不住了,後來果然被人推下台來。不過,二名賤論卻沒就此罷休,竟一直持續了三百多年。便是魏晉以後,單名仍較二名多。
地位僅次於皇族名的是溢號和賜名。“命謚之義,取於尊隆”。諡號是便於人們稱呼故者用的,立謚與否又標明了死者的地位。已故皇上的諡號最尊,官僚臣屬的諡號遠不可與之相比,但比起沒能獲諡號者則要顯貴得多,一般平民百姓絕不可能有此殊榮。至於賜名,則有褒有貶,褒者受寵無比,貶者則賤若三濫。象楊貴妃的哥哥楊釗被唐玄宗賜為楊國忠,沙沱族的朱邪赤心因有功於唐而被賜名為李國昌均是嘉獎式賜名。清雍正皇帝繼位後,詔令與他爭奪帝位的兩個弟弟胤禩、胤瑭(衣旁)分別改名為“阿是那”(滿語:狗)和塞思黑(滿語:豬),則是懲貶式賜名。
賜佳名是皇帝的特別恩惠,凡經賜名的官僚,那名字等於勛銜,高貴無比,人隨名貴,平步青雲,飛黃騰達指日可待。《能改齋語錄》有云:“皇祜中,御筆賜蔡襄字曰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為名者,仁宗怨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字本來不是嚴格避諱的,出於御賜,也成了專利品。賜佳名之尊,如此威風;賜惡名之賤,則如墜入十八層地獄,百般煎熬卻永無出頭之日了。
姓名分貴賤,在宋元時期最為猖獗。清人俞曲園曾引蔡氏家譜注曰:“元制庶民無職者,不許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齒,合計為名。”如今在紹興,仍殘有舊習。如夫年二十四,婦年二十二,合為四十六,生子即名為四六;夫二十八,婦二十四,合為五十四,生子即名五四或名為六九。明代勛臣、昇平王常遇春,曾祖名曰四三,祖重五,交六六;東甌王湯和,曾祖名曰五一,祖六一,父七一,均以數目為名。
宋時里巷細民,亦喜以數目為名,但多為十數以內。如有南陳田夫周三,鄱陽小民隗六,符離人從四。又有山陽漁者尹二、張四、崔三、鄭小五、陳二等,張士誠兄第九四、九五、九六等等。如此測知,宋時同姓名者必定不少。上層仕族,自己有響當的名號,賤民重不重,關他何事呢?封建王朝的專制制度,完全是全心全意為上層服務的呀!
姓名的貴賤如今已成舊跡,撫今思昔,我們真應該多多珍惜自己名字。否則,面對為此奮鬥不息的祖宗,我們怎能不感到問心有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