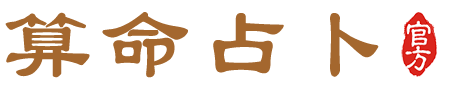說名道姓:十七、姓名與宗教
十七 孫悟空只是個第十輩的小徒罷了——姓名與宗教
“齊天大聖”孫悟空是位婦幼皆知的“美猴王”。悟空乃石破而生,無父無母,更無名姓,孫悟空之名,是佛門菩提祖師起的。
《西遊記》第一回說到菩提給石猴賜姓孫時,石猴“滿心歡喜,朝上叩頭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萬望師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賜個名字,卻好便喚’。祖師道:‘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猴王道:‘ 哪十二個字?’祖師道:‘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叫孫悟空,好么?’猴王笑道:‘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孫悟空也!’”
孫悟空之名,自此流傳千古,播送寰球。悟空是典型的佛教文化產物,乃佛家法名。本文將要論及的,正是姓名與宗教的聯姻問題。
宗教是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絕大多數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從原始靈物崇拜的襁褓孕育漸漸脫胎成形為內涵豐富、體系嚴謹的宗教教義,是一個十分漫長而又充滿鬥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的展開中,宗教猶如文化的母體,其基因潛移默化地滲透浸淫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並繁衍出眾多的的胎兒。許多民族的人名系統都直接受戒於宗教強權的靈光仙氣,大多數人名都染上了強烈的宗教色彩,象孫悟空其名,佛光冉冉,見名聞聲,人們似乎能透過名字而感知到佛寺寶剎的鐘鳴罄響。
宗教對人名的影響,中外有別,梁漱冥先生曾說:“宗教問題實為中西文化的分水嶺。……西洋文化的發展,以宗教若基督教者為中心,中國卻以非宗教的周孔教為中心。”漢民族文化是以儒、道、釋三家的合一。作為“舶來品”的道教、佛教雖然在中國古代社會曾有過出頭露面之日,但最終還是受制於封建禮教的束縛,心苦情願地作了封建禮教的哼哈二將。反映在人名系統中,除了魏晉南北朝佛教初入中國時曾出現過大量同佛教有關的人名外,人名受宗教的影響是很小的。發展到今天,僅剩些盤踞在寺院道觀中的和尚、尼姑、道士們自授些法號、道號,“五行”外人基本無人問津。
西方文化發展走的是另一條路。由於自然環境優越,物產豐饒,他們的先人有更多的閒暇“以騁身外之思”,因而產生了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影響巨大的宗教教派。
以基督教為例。自公元325年基督教被定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後,西方文化的領袖便讓位於宗教。至中世紀,宗教更成為政治上的馭公。政教合一,教會組織遍布全國各地,主教、牧師唱起了政治和日常生活的主角,命名禮、婚禮、葬禮等儀式都在教堂舉行,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人名更是唯宗教色彩是起,聖經中的各路神仙紛紛走入民間,占據歐洲戶籍簿的大多數封面。
在歐洲,幾乎每個公民都是基督教徒,而教徒都得有教名。教名是正式名,必須到教堂去起,教名的選擇被限制在《聖經》或教會曆法範圍內,如此起名者就能同某個聖徒的聖名聯在一起,得其庇佑,且能一同升入天堂。基督教會備有專備的聖徒名冊,東正教有2500多聖男聖女,天主教也有500多名男女聖徒,因此幾乎每天都有幾個聖徒的節日,教徒的孩子出生這天聖徒的名字,往往被用作孩子的教名。在捷克斯洛伐克,你迎面就能碰到諸如亞當、夏娃、約翰、約瑟和路易、馬丁、保羅、安娜等等《聖經》中人,而在西班牙,天主教的聖徒象安樂尼奧、弗朗西斯科、路易斯、瑪麗婭、卡門等常常擦肩而過。聖徒之名在歐洲如此頻繁地走下聖壇,以至那裡的同名者不可勝數,在葡萄牙,叫瑪麗婭的婦女車載斗量,無以數計,據稱,“瑪麗婭”一字的複數已成為葡語“婦女們”的代名詞。
為改變重名現象,有些歐洲國家也曾嘗試尋求區分之法。南斯拉夫有人斗膽同時使用多神教的名,結果贏來了眾多基督教徒的咒頭痛罵,經過長時間的唇槍舌戰,最後大家還是以基督教名作為言和的橄欖枝,而多神教名卻被降格處理,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綽號。
伊斯蘭教是阿拉伯及北非、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國教。在那裡,人們能輕而易舉地從他們的家譜或身份證上找到《古蘭經》中的人名。甚至經典中一些專用頌讚真主的詞,也被善做生意的阿拉伯人抄下來取以為名。據美國人希提所著《阿拉伯通史》載,真主有九十九個美名,這九十九句歌頌真主的頌詞在伊斯蘭教徒中廣為流傳,阿赫德、阿希爾、比爾、巴伊斯,目前正是穆斯林最常用的名字。為避免重名,穆斯林們也常將《古蘭經》里其他人名用作現實姓名,家穆罕默德,易卜拉欣、麥爾彥等即是如此。還是為了避免重名,有些穆斯林取此下策:將姓名染上濃烈的伊斯蘭教色彩,如艾哈邁德(令人欽佩的)、阿里(崇高的)、海珊(美好的)穆巴拉克(吉祥的)。伊斯蘭教徒如此膜拜真主,以致提到教會領袖的名字,都要先嘀咕一番禱詞。愛屋及烏,對曾去過麥加朝聖的穆斯林,稱呼他們前都要加上“哈吉”詞,以示敬重。
印度、尼泊爾、高棉、印尼、緬甸等南亞和東南亞國家是佛教和印度教的勢力範圍,因而這些國家公民的姓名也是佛光靈現。高棉人篤信釋氏,不論高宮顯宦還是里巷草民,一般都得出家修行三月以上。出家者同時被饋贈一個新的名字:巴利文的法號,法號獲得後,即使親生父母也不許呼其原來的欲名,甚至在他們還俗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仍稱其為“班德(博士)”,因為他們深信,進過佛堂的人渾身上下都沐浴了佛祖的光輝,萬萬瀆褻不得。與柬相鄰的緬甸佛門弟子也遵守著如此這般的清規戒律,佛教源地印度當然更是如此。
在印度,與佛教“平均地權”的還有印度教。印度教的主要神名如羅摩、梵天、濕婆、因陀羅、剋星希納等亦被廣為使用。教徒們一般只在擁有幾個甚至十幾個名的神中選其一個為名,但印度人名大多由兩個或三個詞構成,因此有人乾脆在姓名中挑選幾個神名合而成名。如有把羅摩之妻悉達合為一名叫悉達羅摩的,有把克里希納的情侶拉塔共用叫作拉塔克里希納的,有幾個神一起來保佑自己,何患之有?
正如戰爭能夠依仗兵戈臣服異域一樣,宗教也會使用各種手腕謀求在一些本民族文化根基不牢的國家和地區輪流執政。宗教色彩的人名成為記述宗教征服史的最佳史箴。公元初,印度教風摩印尼時,“蘇加諾”、“蘇米特羅”、“卡爾塔 ·古蘇馬”等梵文語式的人名在爪哇族、巽他族人中就很有市場。而14世紀前後,伊斯蘭教東漸印尼,阿卜杜拉、阿里、穆罕默德等頌揚真主的美名於是在蘇門答臘地區占了上風。到了16世紀,西方強權攜著基督精神入侵印尼,人們又轉而爭先恐後地起名“威廉”、“阿貝德·羅沙里約”、“安東尼斯·帕爾萬托”等。宗教的這種變異和取代不僅在印尼表現傑出,在亞、歐、非等其它一些地區也有過“驚人的相似一幕”。
與外國不同,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就一直規範在封建禮教的范囿之中。雖有佛教傳入,異族侵略,但這股文化發展的主流如長江之水,不改其向“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巍然不動。”許多傳教士、布道徒曾試圖在九洲方圓內推銷他們的信仰,不是碰得頭破血流,就是怏怏而返,中華民族強大的包容、化解能量使那些虔誠的信徒們望而生畏,甚至不敢問津。
不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大陸也曾有過一段輝煌時期,雖最終免不了曇花一現的境遇,還是造成了一定影響的。這些影響從人名系統發生的變化上可以清晰地窺見脈胳,呂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與佛教》一文中把這一脈胳把得十分精確,文中論及,時人以瞿曇、悉達、菩提、菩薩、羅漢、彌陀等佛教人名或術語直接用於人名的就達36種之多,而用與佛教有關的一個字如“佛、僧、曇、法、道”等同其它字配合成名的,更是多如牛毛。《南北史表》載,當時,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僅次於之字,如烏丸王氏有僧辯、僧智、僧修、僧憚,琅琊王氏更不避同名之諱,八世有僧朗,九世有僧達、僧謙、僧虔等。此外還有叫王曇首、姚悉達、周法僧、殷梵童、姚菩提、蕭摩訶的,這些都是上了史書的達官貴人,至於平民百姓,其泛濫程度就更不待言了。
中國人的生存能力是全球聞名的,這得歸功於他們的“擇優錄用”意識,自漢季佛教東漸,至天朝而盛,佛教中一些常用且通俗的語詞常被善於挑肥揀瘦的時人剔別出來,取以為名,如阿彌陀佛、阿育王、阿羅漢等名稱盛傳後,以“阿”字作發語詞,兼表親昵的姓名破土而出,如阿蟎、阿斗、阿奴、阿平、阿廣等。單論阿奴,周漠、周仲智就皆用阿奴作小名。史書曾言,齊武帝臨崩,執廢帝手曰:“阿奴若憶翁,好做梓宮。”又劉尹撫王長史背道:“阿奴比丞相更好”,阿奴是王蒙的小名,可見阿奴之盛。
唐宋之際,佛教為儒學所同化兼併,雖鮮有詩人王維、字摩詰之類的佛門殘羹,但釋宗的不出家修行,自性成佛的教義,因符合漢文化的傳統,卻為人所尚。人們不屑在名、字中取道佛釋,轉而效仿南斯拉夫舊習,在自號中洞明與祥宗的依依情絲,如“居士”為佛教“家主”的音譯,代表不出家而受過“三規五戒”的佛教徒,唐宋文人慕其雅致,常托“居士”自號的詠志,如李白號青蓮居士,白居易號香山居士,蘇軾號東坡居士,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司空圖號耐厚居士等,連當初對佛教頗有微詞的歐陽修亦號六一居士,“居士”何其多哉!
唐宋以後,明清人紀承了在自號中“求神拜佛”的傳統。如明陳洪綬號雲門僧、林時雍號常真僧,李貞號大呆和尚、方以智號藥地和尚;清金農號小出家庵粥飯僧、釋道濟號苦瓜和尚又號瞎尊者,許希沖號未了頭陀等等,諸如此類,均是些身在“人間”心在“佛”者思想影點的曝光。
中國幅員廣大,民族眾多,文化淵源參差不一,宗教的影響也強弱有別。公元七世紀,松贊乾布在他的兩個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爾墀尊公主的影響下,信了佛教,自此,佛教迅速散遍世界屋頂這塊神秘的土地,並發展演化成為特殊的西藏佛教即喇嘛教。西藏佛教與西藏封建奴隸主相結合,產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一直延喘到本世紀50年代初和平解放時才壽終正寢。作為文化鏈條重要一環的人名,以其獨特的記錄方式,貯存了這段香火鼎盛的高原歷史。
解放前,藏胞幾乎全民姓教,名字一般都要由活佛、喇嘛來取。佛教諸神、聖者、大師之名,讚頌弘揚佛法的語言等,大多鏡像在人名中。如扎西(吉祥)、卓爾嘎(菩薩)、央金(天女)、取品(興法興教)等即是如此。
對喇嘛、活佛等德高望重的人,不能直呼其名,須在本名或副名前冠以出生地、官街、學銜等尊稱,我們熟悉的達賴、班禪就是尊號,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這兩個尊號的來歷和含義。
1652年,五世達賴入京朝拜清皇。回藏途中,順治皇帝專派特使,攜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刻寫的金冊金印,封達賴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聖識一切”為漢語,表受封者佛學知識博大精深、無所不知;“瓦齊爾達喇”為梵語,原指金剛菩薩,表意堅強;“達賴”是蒙語,意為大海;“喇嘛”則為藏語,意即“上人”,和尚之謂也。整個稱號的大意是:無所不知的堅強的像大海一樣偉大的和尚。“班禪額爾德尼”是1713年康熙帝賜封西藏黃教首領五世班禪的封號,大意為:學識高深的珍貴的大學者。
同其它一些信仰宗教的國家和地區一樣,藏胞的重名現象也極為普遍,往往一個村莊、一座寺廟就有十多個同名者。鑒此,藏胞中又出現了人名中的另一子系:渾號,藏語叫“倉芒”即在本名前冠以地名、職業、性別、生理特徵等文字。如亞東旺堆、仁布旺堆,此為地域分名;興索(木匠)強巴、安姆吉(醫生)格桑,此為職業別名;巴桑(胖子)甲巴,此為特徵異名。
在諸多宗教流派中,中華民族只有道教敢於向佛教提出平分秋色的非分之想。受道教影響,神道之名也偶見書史,但基本上限於字或號中。如唐代李端字藥王、名將李靖亦字藥王;唐賈島號浪仙、宋姜堯章號白石道人等,在此就不加贅述了。
本章主要談了宗教對姓名的影響和重構,至於宗教中人的名號,如法號、道號等,則專有一套清規戒律,鑒於前文已有專述,在此也不犯重嫌了。
張岱年先生曾指出:“在西方,在印度,宗教成為文化的中心,尤其西方中世紀是這樣,雖然中國有佛教、道教等宗教,但都不占主導地位,占主導地位的是哲學思想。”這一觀點,反映在人名中,即可用作國人姓名為何多帶強烈的封建禮教色彩而稀少鏡像佛道的詮釋,我們把這句話為本文作結,正是要大家回味全文,增強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