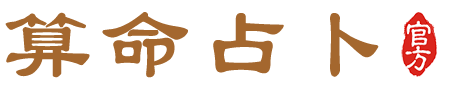說名道姓:八、姓名與禁忌
八 直呼其名者殺無赦——姓名與禁忌
半個多世紀前,美國著名的民俗學家A,s.蓋希特先生曾講過這樣一段話:“許多落後民族保存的歷史傳說沒有超過一百年的。原因很簡單:禁止在談到死者本人及其行為時直呼其名,違禁者甚至要被處死,這就足以隱匿一個民族內部的一切歷史知識,因為,不讓人寫出人名,怎么能寫出歷史?!”
在A·s先生看來。名字的禁忌成為切斷歷史傳說根源的罪魁禍首,那么,人名的禁忌到底是怎么回事?為什麼要對人名行之以禁?人名禁忌又給歷史和語言文學史、文明史裝上了怎樣的調控閥呢?本章將要討論的正是這些問題。
人名禁忌是與人名崇拜密切相關的,受人名圖騰和其它諸如此類的迷信的、宗教的思想影響,古人把名字看得很神秘,以為名字和它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間不僅是思想概念上的聯繫,而且有著實在的物質聯繫.人名是同人的肉體、靈魂緊緊結合、不可分割的,從而惡意的人就會通過巫術詛咒敵對者的名字,造成如同損害其機體一樣的破壞效果。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許多部落中,至今仍有這樣的信念,並由此產生了許多隱瞞和更改名字的奇怪規定。
這些“奇怪的規定”就是關於人名的禁忌。這裡我就個人名字、親戚名字、死者名字、國王及神名的禁忌五個方面來進行辯類分析。
第一類是個人名字的禁忌,這類又分兩種,一種是禁己不禁人,自己不可隨意講出自己的大名,別人則但說無妨;一種是姓名大家禁,誰都不能暴露自個或他人的名字。
在東印度群島,沒人肯講出自己的名字,若揖拳套問居民尊姓大名,得到的答覆往往是顧左右而言問他人。既使在行政和法律事務中,被問姓名的人也是請他人代勞。對這一做法,美國人類學家弗雷澤作了這樣的解釋:“在這些未開化民族的人們看來,一個人從自己嘴裡說出自已的名字,就是從自己身上吐出一部分自我,如果養成不知節制地夸談自己名字的習慣,必將吐盡了自己的精力,毀了自身的健康,終落得體質衰弱,疾病贏瘦的境遇。然而,名字若由別人說出,便同自己沒有血肉相關的聯繫.不會因此而造成什麼危害。”智利某部落的人們,從小就被灌輸上述思想,因而大家都相信,如果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就不能長大,身材就總是那么矮小。
力爭讓別人不知道自己的真名,是大多數原始部落不約而同的默契。在中澳大利亞的一些部落中,男女老幼除了公開的名字外,每人都有一秘密或神聖的名字,只在極莊嚴的時刻才動用一下,平時決不提它,否則,讓不懷好意的陌生人知道了“就更能運用巫術使自己受害。”在這裡,公開的姓名往往是個人的綽號,不屬於他身上的一個組成部分,可以隨便使用且能放心地大膽告訴別人。類似的情況在烏千達的南迪人中也存在,他們對外出參戰的戰士一律呼日飛鳥,同樣地,剛果的班加拉人在打魚前後,不分男女老少,清一色被冠以“姆威爾”的稱謂,至於真名,則是諱莫如深的。
個人名字的禁用,對那些富有好奇心的人無疑是一種刺激,而對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真名則是一種迫害他人的最為有力的工具,當然,那些自認身負教化人類重任的人們,亦可利用它為自己的事業服務。,卡菲爾人深信名字的魔力,並把對名字的手術看成是對其本人手術具有同樣效能的一種措施,他們把年輕竊賊的名字弄到手後,對著煮沸的藥水大聲喊叫這名字,隨即蓋上壺蓋,讓竊賊的名字在壺水中浸泡幾天,這樣,完全不需竊賊本人知道就能取得改造其品行的效果。這當然是迷信,若能如此,今天的法律機構,恐怕得專辟一個藥材和陶瓷倉庫才行。
第二類是親戚名字的禁忌。這類禁忌在國內內陸的某些地區仍留有殘跡,在國外則流落於某些海洋性氣候控制的沿海灘涂或島嶼上。那些有血統關係特別是有姻親關係的人們一般不肯講出彼此的名字,甚至與其名字相似或者有一個相同音節的詞也禁言。卡菲爾婦女不得公開或默念丈夫和其兄弟的乳名,只能用別的字代替,因為沒有任何規則能夠證明那些替換詞的形成軌跡,而那些詞又特別多,婦女人數又為數不少,甚至同一民族的女人都不得使用他人用過的替代詞,必須另找新詞,因而在卡菲爾婦女中形成了一種雜亂無章的特別辭彙,即所謂的“女人的語言”。這種語言給後代的語言學家奉上了一味難侍候的迷魂藥,它們雖然豐富了卡菲爾人的語言倉庫,但後代從庫中取出的卻是一團糾纏不清的混亂。
同樣地,在印尼的巽他群島,居民認為,如果某種莊稼歉收,那一定是田主沒有留心他說出了父母的名字;在荷屬紐幾內亞,努福爾人中男女雙方一旦確定姻親關係,對彼此名字避諱亦即開始,若是誰無意中說了一個應該避諱的名字,就得立即趴在地上說“我剛才說錯了名字,現在把它從地縫裡扔掉,但求讓我還能好好吃飯。”在托里斯海峽兩邊島嶼上,如果誰偶爾不小心講了妻子兄弟或姐妹丈夫的名字,就應馬上慚愧的低下頭去,並且要向被說到名字的人送禮、道歉,以贖愧疚。
第三類是死者名字的禁忌。這種禁忌在目前社會仍很流行,至於古代,則更是無所不在了。分析其動機,主要是怕觸怒鬼魂,當然,不願磕碰心靈深處的傷疤,無疑也是要使己逝去的名字蒙上淡忘薄紗的原因之一。
維克多利亞人從不提死者的名字,即使提起,也只壓抑著噪音稱之為“逝去的人”或“那不再在人世的可憐人”。他們認為,如果談起死者的名字,就會激起Couit一gi1(死者鬼魂)的憤恨,而死者的鬼魂總是在地球上徘徊流連很長時間才走向西下的夕陽里去的,所有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都以提死者名字為大不敬,若斗膽犯禁,則賜之以死,若要保住性命,就得破財消災——通常是趕出兩頭或更多的牛作為罰金。
那么,若有生者不幸與死者同名,那該如何是好呢?果斷改名是唯一的可行之道。北美印第安人凡與新亡者同名一律要放棄舊名,在首次為死者舉行弔唁活動時另換他名。不僅如此,西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如果誰家出了“白喜事”,全家都得另取他名。他們認為,“死者在天之靈若聽到這些熟悉的名字,會懷念親人,重返人間,帶走更多人的生命。”
比起北美印第安人,還有更不幸的事,那就是死者的名字是些人人要用的常用詞,碰上這樣的情況,常用詞也得為死者讓路,另謀新詞,這類新詞的唯一貢獻是,它為語言變遷提供了有力的動力,因為這類風俗影響所至,許多舊詞不斷被淘汰,新詞則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不少部落因此語言總是在變化著,並湧現出大量的同義詞。同時,由於死者名字代表的常用詞被廢而不用,許多詞永遠失去了原義而消失,或者另賦新義而復存,本民族的語言無形中被注入了不安分的血液,成為“創造歷史”的阻力,破壞了民族政治生活的連續性,使過去的歷史記載舍混不清或不大可靠,因而也引發出本文開頭民俗學家A。s先生那段義憤填膺的話。
第四類是國王及其他神聖人物名字的禁忌。毋庸置疑,他們的名字正如其不可撼然的地位一樣,不能損之絲毫。許多國家的帝王授意其御用文人,制定了一系列關於保護王候將相聖名的極為嚴厲苛刻的規章制度,在暹羅,任何人膽敢說出王候的聖名,就將被投入大牢,事實上,由於嚴格的保密措施,平民百姓是很難知曉國王的大名的。暹羅人談到國王,只能用一些響亮的頭銜、稱號如“威嚴的”、“完美無缺的”、“至高無上的”大帝、天子等。祖魯族有一位酋長名叫蘭伽,意思是太陽,該族人只得把太陽改為伽那,現在,酋長己作古一個多世紀,太陽仍在祖魯族的頭上播撒光明,可族人仍不敢把太陽恢復蘭伽舊名。
在馬達加斯加各地,流行著避聖諱之風,馬達加斯加人沒有姓,他們的名字幾乎都是從表示一般事物行為或性質的日常生活用語中選取的,如樹木,花草等等,一旦某種花草被部落酋長相中,取為名字,這個詞就會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而不得隨意濫用。稱之為愛屋及鳥也罷,雞犬升天也罷,反正你得遵紀守法,不可越雷池半步。到毛利的旅遊者若事先弄清那裡的避諱知識,就不會因同樣的事物在那裡鄰近的部落里有許多不同的名稱而徒費口舌了,毛利人的邊境線上應多辟幾個介紹這種風俗的書店才是。
古代希臘,祭司和其他高級官員的名字是受法律保護的,稱呼之,則繩你以法。許多祭司的名字被刻在銅牌或鉛牌上扔進海底,這樣做的意圖無疑是要將名字秘密地藏起來,還有什麼比沉入海底更可靠呢?說句題外話,還有什麼比這種習俗更能昭示古人非物質的和物質的、名字和物質之間的混亂呢?
最後,讓我來剖析一下神名的禁忌。原始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想像創造了自己的神,造神運動一旦形成了固定的神,神名將被秘密地確定且終生保密。否則,他們以為,其他神祗甚至凡人弄到神名後就會藉符水禁咒來驅遣他們。
古埃及流傳著如此一個傳說:凡女伊希斯為了享仙福,偷偷地把太陽神拉流下的口水和著泥土捏成一條青蛇來攻擊神拉,迫使無法經受痛苦煎熬的拉神發誓說:“讓我的名字從我胸中傳到她胸中吧”。於是,伊希斯獲取了拉神名字中所內合的神秘力量,並因此成了諸神的皇后。
這個傳說為古埃及的神名禁忌提供了生動的例證。他們的觀點是,神的真名同他的神力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並且差不多是深藏在其胸腔之內的,似乎是比五臟六腑更為重要的一個相當於靈魂的物質器官。伊希斯就是用一種成功的外科手術剝離出拉神的名字的,每個埃及巫師都深信,誰要是占有了真名,誰就能占有神或人的真正實體並且能迫使他服從自己,就象耕牛服從農夫一樣。所以許多巫師一生都致力於攝取神名的鑽營,費盡心機,不遺餘力。
與希臘一衣帶水的羅馬人也對巫術之於神名的作用深信不疑。當他們圍攻某座城池時,祭師們的任務就是向護城的神祗致詞,祈禱這些神祗放棄被圍困的城市轉而歸附羅馬人,並將因此受到隆厚的禮遇一一比如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羅馬護城神抵的名字都嚴格保密,諱莫如深,以防共和國的敵人開出誘人的條件來引他上鉤,有一個名叫索拉那斯的人就因斗膽泄露了神名而被祭奠了絞架。
以上五類基本上講述的都是外國各民族對名字的禁忌。說到我們中國,關於名字的禁忌更是如山之棘,比比皆是,並因此演繹出許許多多欲言難罷的尷尬和悲劇。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對他人直呼其名在我國仍是一種沒有教養的粗俗之舉,文明人都是避名而喚字的,如蔣介石,其名曰中正,介石只不過是他的字,若是誰當其面而中正長短的,保不準落下一身“洋希匹”的碎唾,這種避名稱字的現象其實是禁忌觀念在作崇。至於在我國古代大行其市的避諱之風,則更是直接滋生於禁忌之酵母了。避諱的產生和發展甚至改變了一部分人的命運和幾個階段中國的語言文學史、文化史,關於這個問題,本書有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