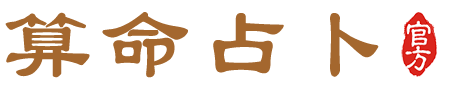說名道姓:七、姓名與避諱
七 明朝為何不準養豬——姓名與避諱
這是一則從三國時期流傳至今的幽默故事。
有一天,張九和李九一個拿著一把韭芽,一個拎著一壺二鍋頭,去找老朋友王九喝幾盅。正巧王九外出未歸,只好讓他的媳婦代為轉告。
王九回來後,兒媳婦對公公說:“張三三,李四五,一個提著連盅數,一個拿著馬蓮菜,來請公公赴宴席。”王九聽罷,一張老臉樂開了花。
王老漢的媳婦搬弄如簧巧舌,將公公名字同音的字一一作了變換,既正確表達了意思,又避了公公的名諱,王老漢找了個深諳避諱之道的好媳婦,他,樂得其所。
《辭海》“避諱”條云:“封建社會對於君主或尊長的名字,避免寫出或說出叫避諱。”
避諱是我國人名系統的一個重要文化現象。“自殷以住,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為之諱名。”可見,我國人名的避諱在周代已見濫殤。目前,流行於人名學界的論調著遍地把避諱孤立地冊封為中國人名系統的一大特產。其實,避諱在國外也曾有過不短時間橫行霸道的歷史,關於這一點,以及避諱的原因,作者本書別有論述,在此不作贅述。
避諱始於周,“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典禮》載曰:“名字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明文規定取各之避。後來,《左傳》又作了一番誇張的引申,加上“不以畜牲,不以器帛”條款,正式宣言“六避”。
避諱分天子諸候死後的“公諱”和士大夫老百姓對尊者的“家諱”兩種。周人雖明令“六避”,但並不十分嚴格,控制範圍也極為有限。“家諱”且不談,條令條例規定的“公諱”,周人似乎都不太放在心上。例如“不以國”條,規定的是不以本國,外國則不諱,於是有了衛候鄭、陳候吳、衛候晉之類投機取巧之徒,但周貴為天子,是各國所共敬的,而《左傳》襄公十五年,“晉侯周卒”,晉候名周,便是有意犯規了。另我國的思想家莊子名周,以“周”的國名為名,亦未見棍棒加身,只是他的不肖後輩中出了個漢明帝劉莊,硬將莊周的莊性從墳中挖出來,改以為嚴,把莊子叫了嚴子,莊子縱然百分地逍遙,冤魂化碟,恐怕也是只愴世之黑蝴蝶了。
周朝據政,雖有天下一統之名,而無上下一同之心,諸侯各國,兵戈相見,冒上不韙者,大有人在。“世亂不知禮,”因而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不以隱疾”條,晉成公名黑臀,楚公子名黑肱,鄭莊公名寐生,均是有意無意與規條唱對台戲。再如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都是不合“不以日月”條款的。周君自顧不及,哪有閒心思去為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動腦子,只好請史官斥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之訓,睜隻眼,閉隻眼罷了。
“周人以諱事神”,在應諱的死人名單中,周天子無疑應發表在頭版頭條。事實上,《周禮》也規定,周王死後,宰夫要手搖木鐸,高唱“舍故諱新”的命令。照說,周代朝庭中對“上諱”應該是十分謹慎的吧,然而且慢,翻翻歷史,周朝自身也是頻頻越位的。像周厲王名胡,周僖王名胡齊;周穆王名滿,周哀王的子孫中有名王孫滿的,都是觸規之舉。上引下效,上樑不正下樑歪,若說周朝行政不嚴,是怪不了別人的。
歷史的車輪總是要滾動的,滾動的過程中免不了要軋進一些橫生歪長的雜碎,腐臭之如避諱,在周末實應隨周之悼亡而壽終正寐。然而,漢代以後,隨著封建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儒家思想的受幸獲寵,避諱之風卻越刮越盛。應該說,避諱的真正根源,並非周禮,而是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倫理道德觀的偏房扶正。此後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中,避諱作為一種特有的人名文化現象繁衍枝蔓,常盛不衰,愈演愈烈,一直揚威至清朝最後一座皇宮關門大吉,才無可牽何地坐上了冷板凳。
漢以後的避諱,按不同級別分成三種形式。首曰“國諱”,專避帝王;次曰“聖諱”,忌同聖人;三曰“家諱”,澤及個人的列祖列宗。如“國諱”,漢高祖劉邦,漢代人避邦代以國字;姓氏中的邱本應為丘,因犯“先師孔聖人”“聖諱”被欽定為邱;杜甫母名海棠,乃不作詠海棠之詩;蘇軾祖父名序,為文均將序改為敘,如此種種,不勝枚舉。歷朝歷代的諱制和諱禁張馳密緊,橫陳豎列,實在難分涇渭,為讀者閱讀之便,本文將避諱方法分為改姓和改名兩大類,別而敘之。
先說說避諱改姓。
姓本不在避諱之列,先哲孟子曾教導說:“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但在孟老屍骨未寒之際,避諱改姓之風即冒了頭。戰國時,宋武公名司空,姓司空的被迫改姓司功;晉僖侯名司徒,司徒便被改為司城。宋武公和晉僖侯乃避諱改姓的“頭俑”。
春秋以下,人口繁衍,姓氏隨之。那時提倡多生多育,因而王侯將相充斥,比比皆是,避諱改姓亦是越避越難避,越避越複雜。且論漢代,楚霸王項羽名籍,籍姓只好改為席;漢宣帝名詢,荀詢同音,荀姓只得姓孫,連他們的先人荀卿也被冠以孫卿。漢代還有姓慶的,此前似有“慶父不死,魯難未已”之說:所幸漢安帝其父名慶,慶姓被改為賀,慶氏子孫不必“愧姓慶“,不知是否真該慶賀慶賀。
唐乃盛世,歌舞昇平,國泰民安,四方來朝,“飽暖生淫逸”,因而避諱之風大發。李姓一跨上寶輦,便明令天下,禁食鯉魚。鯉,河鮮之美味也,唐人因皇上姓李而食不甘味,只得“舍魚而取他味者也”,冤莫大焉!唐太宗因叫了李隆基,於是以盛代隆,以本或根代基,姬基同音,姬姓都姓了周,若是皇上聖諱李隆楊,楊貴妃是否會改叫周貴妃呢!不得而知。玄宗的後代武宗和憲宗,一位名炎,避及啖,啖姓逼改為澹;一位名純,竟避及淳于,淳于姓改為於,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唐宋元明清。唐後大朝乃宋,宋承唐業,亦承唐諱。北宋大臣文彥博,先祖本姓敬,因避石敬璜諱,其祖父改姓文。至後漢,複姓敬。但到了北宋,又因宋太祖趙匡胤祖父趙敬諱,其祖父又不得不改姓文,敬字雖好,奈何“敬諱”難違呀!與文彥博腥腥相惜的同朝匡姓,為避趙匡胤諱而姓了主,不料宋徽宗又覺得老百姓姓主似嫌不敬,硬將主改為康。幸好宋朝坐龍庭時日有限,康姓後裔才能得以姓歸原主。
皇上是真龍天子,喜則百花盛開,皇恩浩蕩;怒則天動地搖,哀鴻遍野。若是龍顏不悅,什麼缺德事都做得出來。據傳宋高宗一日翻閱批文,偶見一制置姓金名賦,望文生義,聯想到金國之惡,如有梗刺喉,筆一舉,給金邊上添三點水,改為淦,一洗金恥,今日江西淦姓後代,多源於此。又說月中嫦娥,本名 娥,唐代大詩人李白詩中就有“白兔秋復春, 姮娥與許鄰”之句,道盡 娥寂清之衰怨。宋真宗趙恆繼位後,文人墨客向玉兔上了討伐書,逼姮娥改名嫦娥,那怕你是閬苑仙芭,也要拉下來守人間規矩。
再說明朝,出了個叫朱元璋的皇帝,元姓因此在人間匱跡多年。且明在,安得元朝捲土重來?因而元來一詞亦被改為原來。明武帝朱厚照有乃祖遺風,為弘朱姓之貴,發文在全國禁止養豬,禁食豬肉。豬者,肉食之大宗也,皇上豈不是連百姓吃飯、吃菜的權力也給剝奪了。
比起避諱改姓之禁規來,避姓改名則更顯豐富多彩,因而也更加茺唐滑稽。因為改換的姓畢竟屈指可數,變來改去逃不過千家姓的苑囿,而名則是隨著人類的生長繁衍而膨然博浩的,同姓者多得上億,同名者則為數寥寥。
對於諱名的方式,古人亦有講究。於生諱名改稱、諱名稱字,於死者則諱名稱謚,無謚可稱者盡可訥而不言,或代之以“亡X”,用不著擔心別人說你不善言辭。
諱名之法,以改字法使用最廣。所謂改字法,即將與應諱之名相同名字的字詞改換為其它文字。看過《三國志》的人都知道張壹其人。其實,張壹本名張懿,只因晉武帝司馬炎祖父是被孔明“空城計”弄得臭名遠揚的司馬懿。作者陳壽生乎其時,不敢違聖諱,因而將張懿作張壹。司馬懿有個窩囊兒子叫司馬昭,魏帝曹髦曾說:“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司馬昭死後數月,沾了其子司馬炎的光,被追尊為晉文帝,東晉人因此不敢名昭,連漢代的王昭君也被改為王明君,《昭君》曲亦隨之變為《明君》曲。另陶淵明曾名陶泉明,鮑照曾名鮑昭,王士禛曾名王士楨,均是“上諱”作案,避道改字使然。
空字法是最為偷懶的避諱方法,只需將應諱之字空而不寫,或代以“某”、“諱”字樣即可。
空字避諱法由來已久。《尚書》載周武王病重時,周公妲祈求三王在天之靈,請以自身代武五去死。禱詞開宗明言:“若爾三王,……以旦代某之身。”某者,周公兄弟武王姬發之名所代也。《宋書》有言:“荊州刺史宣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即是用“諱”字指代宋帝“義隆”之名。東漢許慎所撰《說文解字》,對東漢開國光武帝劉秀到許慎的皇帝劉祜五位皇上之名(秀,莊,恆,肇,祜)皆空字,只注“上諱”二字,更不加音、形、義方面的詮釋。沈約修《宋書》,劉裕皆寫成劉 ,用以替代南朝宋武帝劉裕。
避讀空字極易造成史病。唐人寫《隋書》避李世民諱,將王世充、徐世勣分別寫成了王
充,徐 勣,中空一字,不懂為諱之道者,常誤抄成王充,徐勣。後來,皇上似嫌不甚過意,茲將徐世勣賜姓李,李世勣報之以李,乾脆改名叫了李勣。不過王世充的命就沒李勣那么好了,據說他本姓支,不知為何改姓了王,後來降唐,被仇人所殺,死後並未有所追謚。
避諱的第三種常用方法是缺筆法,即對所避字動動手術,最後一筆缺而不書。你敢犯我上尊的名諱,就得付出一條“腿”的代價。
因諱改名不僅涉及人名,甚至“澤”及地名、官職名、事物名、書名等。按照諱之祖制,周代命名“六避”是應該讓道於官、山川、牲畜、器幣的。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後世的帝王之胄都不吃這一套,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僅故意取以為名,而且要山川之類避其聖諱。
五嶽之一的恆山,一度改稱常山,就因漢文帝大名劉恆。戰國時的魯國出了姬具、姬熬二位君主,魯境的具山、熬山即告易名。宋太祖趙匡胤亦將匡城縣、胤山縣統統改掉。南京曾名建鄴,司馬鄴登基後改為建康;玄武湖曾名元武湖,因清一朝有康熙皇帝玄燁。如此種種,均是諱及地名的例證。“六避”云:“以山川則廢主”。在這些達官貴人看來,主可廢,聖上的大名是萬不可動其一毫的。
“六避”又云:“以官則廢職”。晉僖侯名司徒,於是先廢司徒官職,後雖恢復而改稱中軍;唐太宗名李世民,改民部尚書為戶部尚書。正所謂“刑不上大夫,”黃泉路人其奈我何?
至於因諱名而改物名、書名等,更是將世間物事搞得一團糟。二十四節氣之一的“驚蟄”原本叫啟蟄,是避漢景帝劉啟諱而改稱的;野雞本叫雉,漢高祖呂后取雉為名,於是才有野雞一說。比起這些來,改改書名就不足為奇了。《廣雅》一書因揚廣而改名《博雅》、《太玄》一書因唐熙玄燁而改為《大園》,實在用不上到衙門口去擊鼓。
歷史是一部宏偉的交響樂,有起有伏,有張有弛。避諱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亦然。南北朝就是避諱史上的一個特殊時代,他們似乎專門以同名不諱來自鳴高尚,且看書法大家王羲之一家三代的行輩表:
玄之
凝之
羲之
微之
楨之
操之
獻之
靜之
王家三代不避同名“之”諱,究是原因,當時,之字是貴遊子弟的特別標幟,並極有可能是五斗米道中用於名字的暗記。這正如那些要風度不要溫度大冬天穿裙子的窕窕淑女一樣,為了髦得合時,寧可傷寒抽風。而且就後一點看來,“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頭可斷,血可流,做人的標準是不能倒的。
王家非皇族,似嫌說服力不夠。在下翻閱史卷,輕而易舉又找到兩則“皇”證:齊高祖蕭道成字紹伯,其父就叫嗣伯,;後魏獻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亦名宏,可見南北朝上上下下均是避諱觀念不強的。
避諱這種現象,本身就是能件不正、坐不端的崎形產兒。名不正則言不順。在其歪歪斜斜的前行史上,時時忍不注要爆發些不尷不尬的幽默故事來,倒為中華笑史添了一筆意外之財。
元《稗史》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錢大參良臣,自諱其名,其子聰慧敏達,性愛讀書,凡經史上有“良臣”二字,均避而諱之。一日讀《孟子》“今日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避“良臣”父諱讀曰:“今日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為避父諱,孺子只好認“賊”作父了。無獨有偶,同代某君父名阿谷。一天,此君讀《四書》,突遇“舊谷既沒,新谷已登”一句,無可奈何,只得高聲誦曰:“舊爹既沒,新爹已登”,諱安全避過,又給老爹送了頂綠帽子,阿谷取此名時,是否科到會有如此“名”外之獲呢?歷史上,關於馮道和田登避諱的笑話是廣為人知的。五代時馮道的門客讀《道德經》“道可道,非常道”之句,因為要避馮道的諱,遂鄰居民了“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一時傳為笑談。老師的“道”字尚且如此“不敢說”,要是避皇上諱,真不知這位可憐的學子該如何去說了。田登是宋仁宗時的南宮留守,登兄治州無甚造化,於避諱卻頗有造詣。“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放火三日。’”上元節是行燈會之佳節,白髮垂髫放燈嬉戲,其可快也歟!孰料田登諱登改燈為火,一字之差,性質迥乎。試想,老百姓果真群起而縱火焚物,那還了得?田登後來因此而罷了官,實在是罪有應得。
幽默畢竟是調侃,笑則笑矣,無妨大體。有些讓你笑不出來的諱事,則不得而委屈讀者諸君了。下面說幾個因犯諱而影響個人一生前程、甚至掉了腦袋的恨事,扼腕獠牙,悉聽尊便。
唐代大詩人李賀,文彩飛揚,傲視當代。惜乎其父取了個李晉肅的大名,賀只得放棄中進士的非分之想,進士乃官衙的敲門磚,“晉”都不進,何仕之有?韓愈得知此事後,憤然作不平之鳴,專撰《避諱》文以伸其怨。文曰:“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韓愈憤則憤,徒傷悲白髮,於事無濟,李賀仍被終身攔在進士試場門外,只作了個職掌祭祀的九品小官,鬱郁了此一生。
田登、馮道之流,王侯將相走卒耳。他們手持“為尊者諱”的衛道劍,頂著下屬晚輩的腦門,只能算得上淫威小耍。皇上聖諱之威,則是儀若雷霆,萬萬不可冒犯的。《唐律疏議》規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的就是犯了“大不敬”罪,跨入不赦的“十惡”之條,哪怕是無意犯禁,亦難逃“法”網。明太祖朱元璋當過光頭僧,舉過義軍旗,因此避“僧”,“賊”二字象避狗屎一樣敏且捷。杭州學府教授徐一夔寫賀表時,用了“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之句,朱元璋看勃然大怒,說:“生者僧也,以為我從釋氏也,光則摩頂也,則字音近於賊也,罪坐不敬。”將徐氏的頭祭了劊子手的屠刀。
清朝雖是滿人坐龍庭,視漢人為劣質公民,對漢皇的一套封建禮制卻全部奉行拿來主義,並且加上了自己的改良和發揮。乾隆時,江西舉人王錫侯修訂《唐熙字典》,自編《字貫》一書。巡撫海成發現書中竟直書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心中竊喜,趕緊上告皇上,以為能賜官受封,連升三級。不料乾隆的想法大出海成所料,他不僅下令斬了王錫侯及其子孫,連海成巡撫也冠以未能明言《字貫》凡例中的“大逆不法,罪不容誅“之罪,革職查辦,最後還判了斬刑,緩期執行。甚至連海成的上司兩江總督、江西布政史、按察史等也受了株連。海成巡撫身陷囹圄,連自己拿靴子掌嘴的權力都給剝奪了。這位拍錯了馬腿的仁兄真該”以頭搶地爾。”
犯諱受刑的事例說明,受封建禮教文化、等級觀念影響而形成的避諱,一旦羽翼豐滿起來,它又會反過來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產生很大的制約作用。正是人名與文化的這種相互作用,使得人名系統的文化內涵日益豐富多彩,日益複雜深刻。
正如腐臭的東西可用作肥料,錯謬的事故可以借為明鑑一樣,避諱也有能化腐朽父神奇的地方。避諱雖然不愧為製造古典文獻溫和混亂的“精英分子“,但由於它是時代的產物,人們又能反過來利用它去辯別古書、文物的真偽,敲定書籍版本的確切年代。因為某個時代出版的書,都要避當代君主的聖諱和個人祖輩先生的私諱的,明知故犯,則是偽作無疑。
如署名司馬相如著的《長門賊》,開篇首句便道:“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司馬相如早在漢武帝死前32年就魂歸西天了,他是怎么得知劉徹死後的諡號“孝武”呢?《長門賦》顯然是後人偽作的。
再如《六經》一書,署隋朝王通著。但書中卻避唐高祖李淵諱,將戴淵改為戴若思;又避唐太祖李虎諱,將後趙太祖石虎改名石季龍。隋人避唐諱,豈非乾坤倒置?可憐唐代這些偽作者,連偽書都要避當朝諱,雖想天衣無縫,奈何諱之虎?烏呼!
還有一種試析作者真偽的妙法,即書中涉及作者本人“尊者”大名的地方,作者是否避而諱之。當今,《紅樓夢》為曹雪芹所著,似成定論,但看二十六回如此一段描寫,不由不讓人疑竇頓生:
“眾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覺得沒意思,笑道:‘誰知道他糖銀果銀’”。
曹雪芹其祖為曹寅,雪芹把寅字又寫又說,不僅手犯,而且口淫,簡直肆無忌憚之極。曹公如此大手筆,拈字弄句手到擒來,焉能為區區取一名字而犯祖諱?可見,《紅樓夢》並非曹雪芹所著,此證雖孤,卻似歸納推理中的反聲,正如多米諾骨牌,倒其一隻則撲其全體,潘成規此證雖孤卻強。
避諱之于姓名,可謂重頭戲。筆墨所限,本文不能展說,只能勾其大概,讀者諸君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