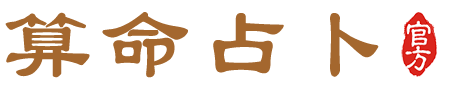說名道姓:六、同姓名瑣語
六、兩個曹操誰是梟雄——同姓名瑣語
許多人都熟悉曾參殺人的典故。曾參孔門高足,孝行第一。一天,他的母親正在織布,突然一個人慌慌張張地闖進來嚷道:你的兒子殺了人!曾母鎮定自若,手不停機:知子莫如母,象他這樣的孩子,怎么會去殺人呢?過了一會,又有一個跑來告訴她,曾參殺人了,曾母手中的棱慢了下來,心中開始有了疑慮。不一會,第三個人氣喘噓噓地跌進門,大叫曾參真的殺人了!曾母驚懍失措,扔下稜子趕緊跳牆逃走。
其實曾參根本沒有殺人,兇手是魯國另一個叫曾參的人。同姓名現象讓曾母擔了場虛驚。
自有姓名以來,同姓名現象就一直如影隨形般在姓名系統中游弋晃蕩,早在南北朝時,梁元帝蕭鐸就親自編撰了《古今同姓名錄》一書,自此,唐、元、明、清代代有人在同姓名上作文章,清乾隆年間浙江蕭山人汪輝祖獨辟小徑,從《舊唐書》到《明史》9部正史中輯錄同姓名者10812個,總計約3萬人,編成《九史同姓名錄》,全書凡七十六卷。僅僅9部史書就蒐集了這么多同姓名者,若再加上載籍之外不見經傳的人物,則更是不可勝數而泛濫成災了。
從《九史同姓名錄》,我們發現,許多著名人物都曾受過犯其名的傷害,如春秋時有兩個毛遂,兩個曾參,漢未有兩個劉歆,漢張良之後歷代都有張良,僅宋代就有9人。其它如叫“周瑜”的4人,李廣的6人,張衡的6人,董仲舒的3人,王羲之的3人,曹操的2人等等。不少同姓名者都是名人,如4個叫王充的人,一位是東漢著有《論衡》的哲學家,一個是越王侗封鄭國公,另兩位分別是符堅中山太守和侍中將軍。漢代的兩位韓信,一是曾受“胯下之辱”的淮陰候韓信,一是韓王信。
同姓名者如此之多,設若將這些同姓名者都當作一人,就會笑語百出;要是治史者將其誤信書諸史籍中,那就不僅僅是鬧笑語了。司馬遷就曾在同姓名的知識方面栽了跟頭,讓孔子弟子宰予蒙了好多年不白之冤。《仲尼弟子列傳》有云:“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事實上,這個與田常作亂的宰我並非孔門弟子宰予(字子我),而是一個叫止(字子我)的人,若不是後來唐代司貞作了一番深入考證,澄清這一事實,宰予的冤案不知要擱到何時才能昭雪了。《史記》還將戰國時趙國以論證“堅白異同”命題聞名的公孫龍,混淆為春秋楚國人、孔子的弟子公孫龍,並非司馬遷要跟孔門弟子過不去,實在是同姓名現象蒙蔽了他的眼睛呀!
同姓名現象最容易發生衝突且帶來種種後果的是同時同地的同姓名者。戰國時,趙國平原君有位了不起的食客毛遂,他曾自薦陪平原君出訪楚國,按劍威劫楚王,定下了合縱抗秦的條約。平原君十分看重毛遂,認為他的三寸舌,勝過十萬師。有一天,忽然有人報告說,毛遂墮井身亡,平原君不由放聲大哭。後來毛遂卻又回來了,這才知道死者是另一個叫毛遂的人。平原君沒有白哭,這么一陰差陽錯,使毛遂更願為他賣命了。東漢末年有一位姓陳名遵字孟公者,熱情豪爽,不拘小節,非常好客,常常在家裡濟聚眾生,飲酒暢談,為了留住客人,每每把客人的車轅投入井裡。當時,列候中有位與他同姓名者,也喜歡串串門,一到別人家門口,司閽的向主人報說,陳孟公駕到,主人及座中客人莫不震動,等到見了面,才知道此孟公非彼孟公也,頓時熱情驟減,因為這事常常發生,人們乾脆給這位孟公送了個綽號曰陳驚座。
同姓名者如果在同時同地,又碰到一起,往往會產生戲劇性的後果,頗多軼聞趣事可作談資,王漁詳《池此偶談》有云:
“小說載李空同督學江西,有生姓名偶同,李出聯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應聲云:‘費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空同喜。”
象這樣科場中同名師生相遇的事例並不罕見。康熙癸丑會試,翰林學士張英為同考官,本房同式中就有一個海鹽的舉人張英。丙辰會試編修馬鳴鑾做同考官,不料在本房同式中也碰上一個河南的舉人馬鳴鑾。老師碰到學生與自已同名,一般說來心裡不會太舒服,常會作“名相如,實不相如”的思考,是否因而影響到學生的考績,這就不得而知了。
從考場步入官場,這樣的例子也不少。《桐陰清語》一書中講了這樣兩個故事。漢代石屏張月樵太史在京師時,有一個與他同姓名的在衡州當縣丞。張縣丞一次進京拜會宗人後準備回衡,張太史得知後,送縣丞詩一首調侃他,詩云:
連天一派無同姓,兩地交稱不異名。
文士時雖分李益,詩人詎豈別韓翊。
丞何曾負慚余拙,叔恐為痴被子輕。
此去衡山尋玉簡,曠懷千古獨輸卿。
無獨有偶,大興徐香坨太史(鑒)知興化府時,有同姓名者署永定興化鄉巡檢,太史孫作詩調侃這位仁兄道:
今仲舒同薦仲舒,名相如亦實相如,
郭淮可與汾陰地,李秀傳疑北海書。
可有小冠能別否?竟同大諫獨何歟?
苦吟寒詩飛花句,與此韓翊或是余。
官場中同姓名的調侃往往是單線的,即上司對下屬。被調侃者還不算倒楣的,史書上就有不少犯上諱者自動易名的例子,也許我們身邊就有,相信你仔細回想一番後,會證實我的推測的。
同姓名者既是如此頻繁,同名就更不待言了。除去姓氏,單列名字,其等同率豈不高出百倍、千倍?
同名者有示仰慕而效同者(後文有述),有茫茫然偶同者,更有以故意效同而心懷不軌動機相反的。《左傳》載有這么一個故事:
文公十一年,狄人入侵魯國,文公就派叔孫德臣率兵反擊,一舉敗敵於鹹陽,俘虜敵主將僑如、豹、虺三人,將三將斬首,埋於子駒門,為使後世了解他的功勳,就把兒子分別改名叫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虺。
把所殺仇敵之名轉讓給自己子孫,是古人紀念戰功的一種形式。成吉思汗又叫鐵木真,他出生時,其父剛剛戰勝塔塔兒部,獲其酋長鐵木真,戰捷得子,是為雙喜臨門,為紀念之即將鐵木真之名加於成吉思汗。
後魏韓延之使用同姓名的方式最為令人叫絕。韓延之魏人仕晉,為平西府錄事參軍,劉裕為伐司馬休之,寫了封密信給延之,要招他為幕僚,延之堅辭不允,為表決心,他想了一妙招:劉裕的父親名翹,字顯宗,延之就給自己的兒子改名叫翹,並自字顯宗,表示誓不臣劉氏,這一招使得不僅絕,還蠻損。不過從另一個方面看,它不失於一種表示不屈從對方、與人深仇大恨的妙法。
景仰也罷,述功也好,示仇也罷,均是有目的而來。無論其效用如何,皆是咎由自取,怨不了他人,最為無奈的,是自己的名字不幸而與趣旨相乖者等同,常如芒刺在背,頗有不適,這事發生在普通人之間尚可不予計較,若是在名人與名人之間,則更有後效前名之嫌,一般得想方設法予以“嚴正聲明”。王安石曾有篇長文,大罵謝安石功出僥倖,其嬌情鎮物全無取處。並一再聲明,王安石之名絕無仰慕謝安石的意圖,安石之同,純屬偶合,要外人不得瞎猜亂議。
王安石後有來者,國民黨元老張繼在為寒山寺俞曲園書寫因“楓橋夜泊”而聞名的唐張繼詩時,曾附短跋云:“……湖帆先生以予名唐詩人相同,囑書此詩,惟予名實取恆久之意,非妄襲古人也。”
姓名以外,還有字號。字號常以述志,然古今同號者雖多,志趣卻常大相經庭。如三變之號,柳永、楊畏、唐五經三人的據之,柳永之“三變”,斷自《論語》子張“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楊畏則是“天下於是目為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佑,遷於紹聖也。”唐鹹通中,荊州書人唐五經號三變,且自釋其義:“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其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其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其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無代之。”唐、柳、楊“三變”,同號異旨也。
《金史》載:“雷淵為監察卸史,出巡郡色,奸豪不法者立錘殺之,至蔡州,被殺五百人,時號雷半千。”無獨有偶,唐朝員餘慶,與何彥光同拜王義方為師,義方常道:“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此改名員半千,賢者名同酷吏號,實在不尷不尬。
又清人筆記小說記述一鐵匠發跡,建巨宅,延請某名士為其命宅名,名士署其堂問:“二西堂”。眾皆譁然,認為某名士命名言過其實,根據是“二西”乃文人書齋專號,如明嚴蔚號“二西齋”等。二西,本指湖山的大、小西山,“舊亡秦人,避地隱居於此,”給鐵匠宅名二西堂,豈非盜文士雅儒之嫌。文士後來解釋說:如此名命,卻是實實貼貼,絕不誇張。細觀西字直立如打鐵的鐵貼,橫臥如風箱,正是鐵匠的家中長物呢。
同樣地,“甲乙齋“似專為文人墨客名號專用。甲乙者,數一數二之謂也。可有一文人卻為一補鞋匠署其宅門曰”甲乙齋“。因甲字似錐子,乙字似切皮刀子,亦是鞋匠家中長物呢。古近代同姓名現象頻繁,由於人口不多,命名方式源廣,還不至於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今,人口膨脹,語言文字的簡化以及冷字眼的摒棄,同姓名現象已成了一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
據報載,上海叫“王小姝”的多到13000多人,瀋陽市現有4800多個“劉淑珍”,4300多個“王玉蘭”。90年代初,廣洲的“梁姝”、“陳姝”各為2400多個,天津的“張力”、“張英”各有2000多個,武漢城區僅16歲以上的常住人口中,叫“王紅”、“王斌”的便超過一千個,甚至在一個單位,叫張偉、李華的就能一打打地出現。倘若不算上同姓,重名者的數量就不止是以千計、以萬計了。據有關部門統計資料:174900人中,重名者達46745個,占調查總數的26.72%。時至今日,重名率更是大幅度上升,如中國體育報評選建國以來80名傑出的教練員、運動中,便有4人名“健”:張健、高健、黃健、韓健。
重名現象在今天如此之多,輔以各種文化的、科學的、技術上的傳播和交流手段,同姓名者碰到一起的機會就大大增多了,各種令人啼筆皆非的軼聞趣事更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
據《光明日報》載,清代查禮《銅鼓書堂遺稿》中有一個同姓名的奇事,這本詩集15卷末兩頁上居然出現如下兩個詩題:題蔣介石處士松林獨坐圖偕朱玉階學使游亡星岩即以志別”。當今中國國共兩黨兩位著名人物的字(蔣中正,字介石;朱德,字玉階)竟然同時出現在200多年前的詩集中,而且一字不誤,真乃咄咄怪事。
40年代的上海市長吳國楨,聽說有個被判死刑的罪犯也叫吳國楨,市長以同名的緣故,打電話到法院訊問罪犯的情形。死刑判決後,法院特抄一個判決書的副本遞送吳市長。有心人作了一番調查,發現當時上海有13個吳國楨,中電公司得知這一訊息後,新聞敏感性大發,遂將這13個吳國楨聚在一起,拍了一部新聞影片,正所謂“有緣千里來同名”。
1994年,以《李雙雙》一書出名的作家李準,在報上發布改名啟事:為了尊重讀者,我今後放棄用李準原名,改為“李凖“。他還聲明:“我的原籍是河南,職業是寫小說和電影,是《李雙雙小傳》、《黃河東流去》等作品的作者”。李準算得上是名作家了,為啥要在報上發布改名聲明呢?是同姓名現象捉弄了他。原來有一天,報刊上出現了“李準”署名的評論文章,許多老作者都打電話或寫信問他怎么寫起評論來,他本人也是莫名其妙。後來方知,這位寫評論的“李準”是與他同姓名的年輕人。作家李準象吃了個蒼蠅般心裡不快,只得改名,惹不起躲得起,出此下策,實屬無奈。
青年李準之名可能是無意偶合。當今有些人,為了一定的目的,常冒名家之名辦事,還真讓他們占了些便宜呢。據說,前幾年某刊物接到一篇署名劉心武的小說,不禁喜出望外,極為重視,但仔細一看,劉心武三字較草,“心”是個連筆字,似是而非,不過,當今文壇,還有其他叫劉什麼武的作家呢,編輯大筆一揮:立即排發!不料,出刊後,作者來信聲稱自己名叫“劉必武”,小說發表誤排劉心武,要求予以更正,編輯部吃了個啞巴虧,有苦難言。
國家游泳隊曾有兩個叫嚴紅的運動員,1985年8月,兩個嚴紅在體壇上傳出一則“嚴紅打破嚴紅記錄”的新聞,她倆一個來自四川,一個來自天津,為了區別,人們分別稱之為“川紅”、“津紅”,1985年8月,川紅打破了津紅創造的200米自由式記錄,成就了一段“嚴紅破嚴紅”的佳活。
社會上同姓名太多了,而產生佳話的卻不多,倒是招惹的麻煩不少,造就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有一則報導講:公安部門在某街道捉拿叫“黃軍”的要犯,殊不知此處“黃軍”有4個,被抓的並非真兇,錯抓的黃軍正在籌辦婚事,其女友一時不辯真相,氣急吞下毒液……”
只因一名同,險鑄人命案,這是事故。
另一則報導則講了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文革”中,某公司召開批鬥大會。會場極為嚴肅、緊張,主持人突然厲聲宣布:“將歷史反革命分子楊志傑押上來!”站在台下的某分廠青年工人楊志傑嚇得臉色煞白,周圍的同事也嚇了一大跳:沒想到身邊埋著這么大一顆“定時炸彈”,這小子才20歲,怎么還是“歷史反革命”,難道他一、二歲就乾過“反革命”的事嗎?正自疑慮,一位五十多歲的人被押上台,胸前掛塊牌子,上書“歷史反革命分子楊忠傑”,並打著紅×。青工楊志傑和他的同事這才回過神來,一場虛驚,同姓名差點敗壞了一個人的名聲。
還有一則報導講某市一家醫院藥房因疏忽而發錯了藥,急須找一個叫王勇的男孩,情況十萬火急。可是在那個不大的地段,叫“王勇”的小孩竟有十多人,派出所只得緊急出動,查戶口問地址忙得團團轉,好不容易才找到那個王勇,差點造成了人命案。
當代人名系統中存在的重名現象,問題十分突出。小而言之,會給重名者帶來諸多不便和不必要的麻煩;大而言之,會給社會生活帶來不少的混亂。尤其在社會進入資訊時代後,重名太多,勢必給通訊聯絡、戶籍檔案、統計管理、歷史考證帶來種種麻煩,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公安、郵電部門的同志歷經千辛萬苦尋找某個人的事跡報導,其辛苦遭遇往往就是重名的作崇。
重名,無疑是當今社會人名系統的一個癥結所在。為什麼如今會出現如此多的重名者呢?仔細分析,有如下原因:
人口的急劇增多是重名的首要原因。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人口成幾何數上升,從抗戰時期的四億,到當今的12億,令人瞠目結舌。人口增多,而人名用字卻隨著漢字的簡化而減少。現代漢語常用字大約7000個,最常用的只有3500個,據查,人名中所用字數為3350個,與最常用量不相上下,但是這些字中有些生冷字眼除極個別人使用外,用者甚單。人們取名字往往集中在那些表達美辭,朗朗上口的幾百字上,如使用頻率最高的英、華、玉、秀、明、珍的覆蓋率即達1%,粗略地估算一下,就是12億人中有1200萬人用這6字為名,即每字有200萬人取以為名,其重名程度可想而知。最常用字的前409個字的覆蓋率達90%,減去少數民族,意味著11億人用這409個字為自己命名,有人計算過,即使這409個字中的每個字都能與所有409個字搭配組成雙名,並且409個字都能用於單名,總共也只能構成167690個名字,由11億人分享這些名字,意味著每個名字要供6020個人使用,如果再考慮一下地區和某些最常用字的使用率,重名程度將更高。
其次,命名方式日趨雷同。在當代,一方面傳統的命名方式基本消失,另一方面,新的命名方式愈來愈簡單化,大致有:(1)以出生地或出生時某些有紀念意義的事情為名,北京多“京生”,上海多“滬生”,廣州多“姝”。一個嬰兒在北京出生,取個什麼名字好呢?許多人會靈機一動,或懶漢思想作怪:既然是北京生的,就叫“京生”吧,也有個紀念意義,英雄所見略同,於是就成千上百地出現了“張京生”、“李京生”、“錢京生”,據說某國小的一個班裡,有四個學生叫“王京生”,老師一叫王京生,四個小孩一齊應聲。為了區別,只好據其特徵叫“胖京生”、“瘦京生”、“高京生”、“小京生”,就這樣,難免不鬧笑語,老師只得請孩子家長為學生改名。(2)命名的求美心理和時代風尚導致重名,如姓曾的會想到曾朝夕,姓楊的會想到楊帆,姓高的會以高昂、高揚等為名,這樣的重名率也較高。另,時尚的作怪,人們又會不約而同的瞄向幾個時髦字,如“文革”時的“紅”字,作名的使用率就由建國前的0.136%猛增至2.151%,大有萬里江山紅遍的趨勢。(3)以父母之姓名合起的方式;(4)節縮成語格言而成的方式;(5)利用語言相疊的方式等等。
取名的方式集中類同,必將造成大量重名。
第三,單名趨勢是造成重名的一個重要因素。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後,單名的比例開始上升,至解放後大有超過雙名的勢頭。通過對濟南市一個普通居民區街道的1000個人名之調查表明,單名的比例從1948年的3.3%到1986年上升到69.7%,幾乎每年都要上升一個百分點。用一個字作為名字,表意較好的字眼重名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晨、亮、悅等,據調查統計,7省市174900個人名中,單名重名率大大高於雙名重名率,21400個單名中,重名的就有17592個,占54.168%,而總數151500個雙名中,重名的僅35153個,占22.901%。
既然重名,何不改個別的名字呢?這不是挺容易的事嗎?然而且慢,並非所有的重名者都願意隨便更名的。一是嫌麻煩,不少人還有這種思想,姓名髮膚乃受之於父母,不願隨意加以更改,所謂“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此乃尋根的文化觀念在潛在地起作用。二是有人認為,人名只不過是一個符號,即便相同,並不能表示真實人物的等同,改不改無關緊要,再則,有人也作這樣的考慮,即便改了名字就能保證不再與人重名了嗎?如果又重名又怎么辦呢?再改,改到何時才能沒有重名呢?在人口爆炸,命名範圍如此狹小的今天,起個不重的名字真是太難了呀!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改名並不是根除重名的好辦法,最可靠的辦法是抓根本,即從父母給小孩取名時做起。一是父母在給小孩取名時要慎而又慎。最好不取單名,儘可能避免與人重名。有人曾在《解放日報》上載文建議,傳統的子承父姓方式應當改變,可改為父母合姓再加名字。這也不失為減少重名的一條重要途徑。據推算,如以1000個常用字來計算,都取單名,那么總共只有1000多個名字,但是如果都取雙名,將這1000字任意排列,就有100萬個名字,如果採取父母合姓再加雙名或姓加三字名的方式,那么1000常用字就可能合成10億個名字了,除去少數民族和雙名、單名,同姓名的問題就基本上得以解決。據《現代家庭報》載,目前,我國已開始流行四字名,如“殷樂笑子”、“沈芳娟子”等,這是一個好的現象,我們應該大力提倡。
二是出版部門應當出版一些取名指南性質的書,用以幫助人們擴大取名字數與選字範圍,台灣出版界在這方面做得挺好。他們已出版了多部取名指導專著。如《命名匯典》、《標準命名寶鑑》、《嬰兒命指南》、《命名參考》等,我大陸的出版界應見機而作,聞風而動,為革除重名作點貢獻。
三、戶籍管理部門也應當做些減少同姓名的工作,例如,設立取名諮詢機構,用電腦貯存本市、本地區以及歷史人物中同姓名的資料,當家長在給新生兒申報戶口時,向他們提供這方面的服務,以便了解新生兒的姓名是否與人雷同,否則就可以及時予以更改。這樣做,還能免去此後改名的諸多不便,聰明的家長也應積極配合。
以上概述了中國同姓名的現狀,在國外,同姓名現象也是十分嚴重的,如有人開玩笑說,俄國女人不是“娃”,就是“娜”,男人不是“斯基”就是“洛夫”,不僅俄羅斯如此,許多宗教的國家都是如此,這在《姓名與宗教》一章中有述,在此不贅。